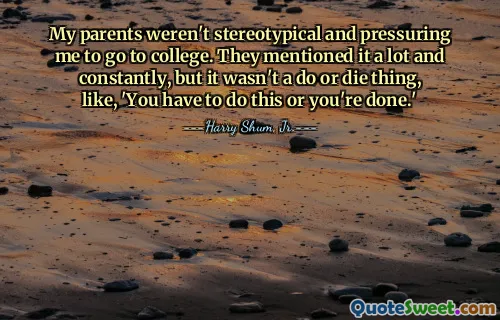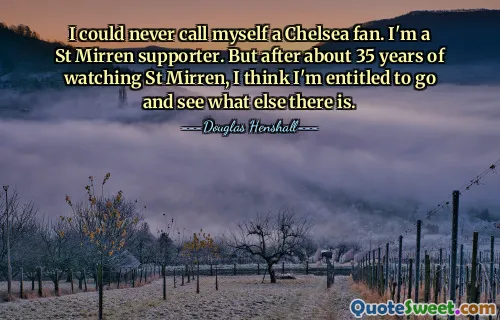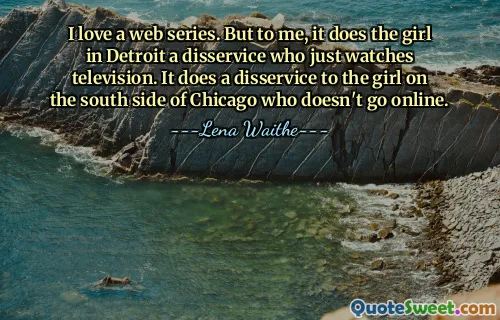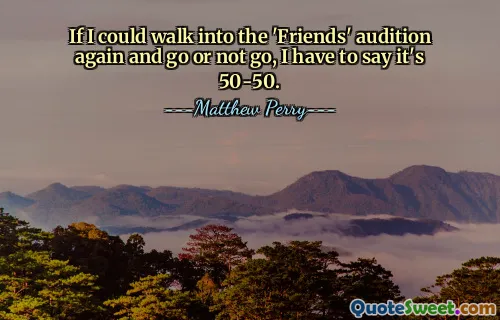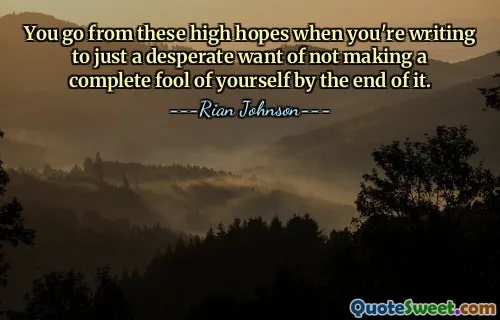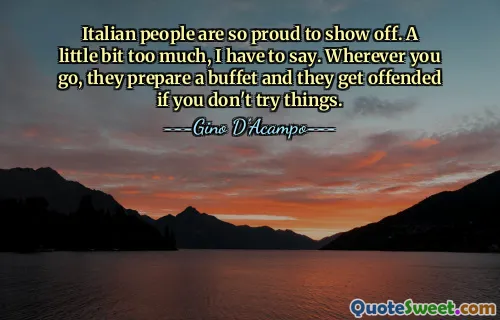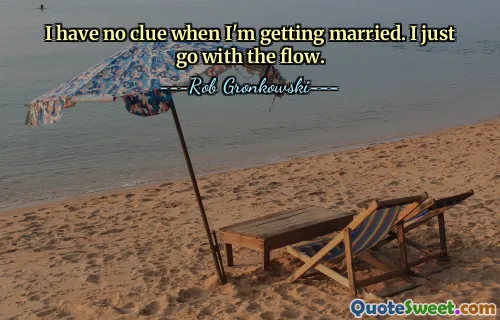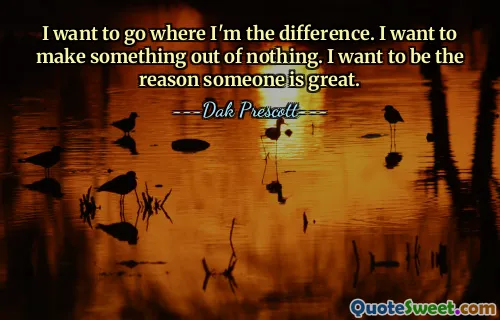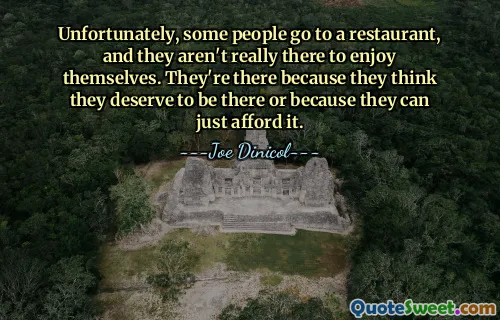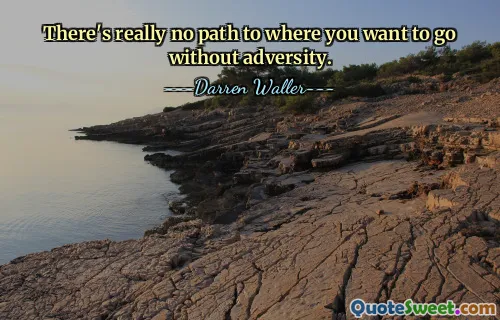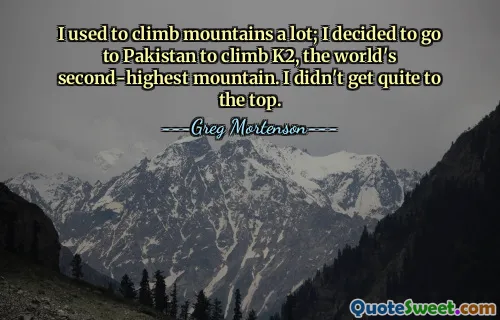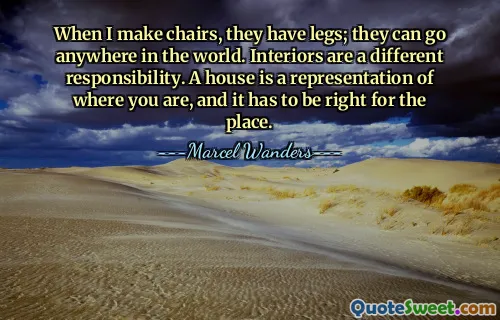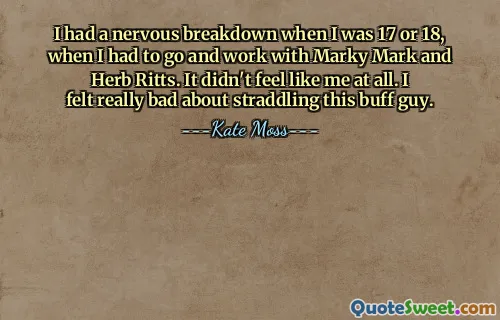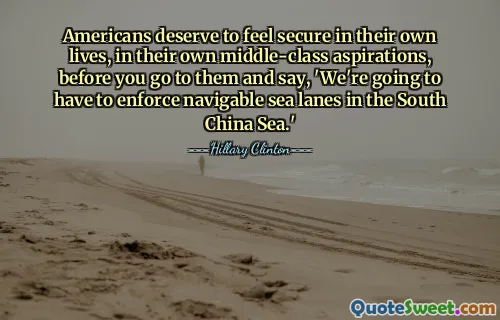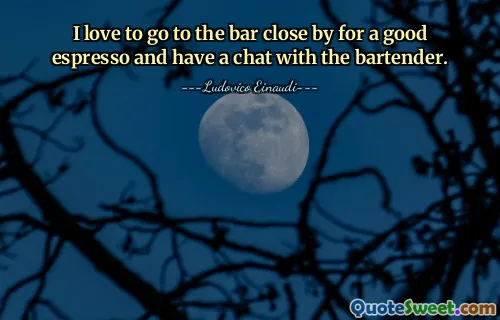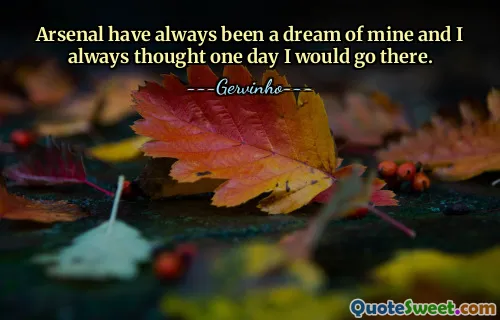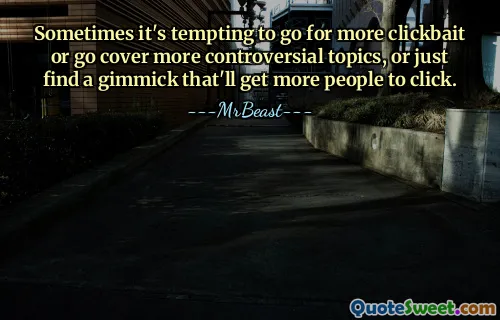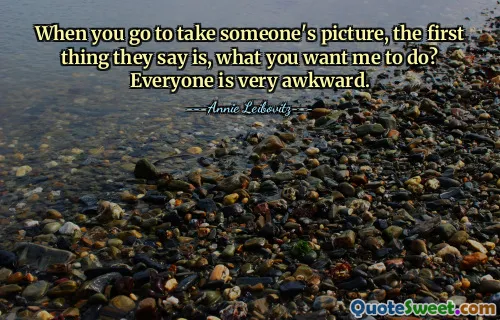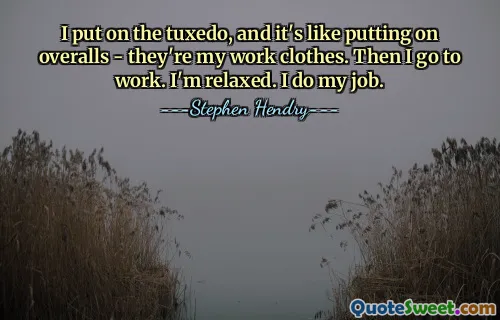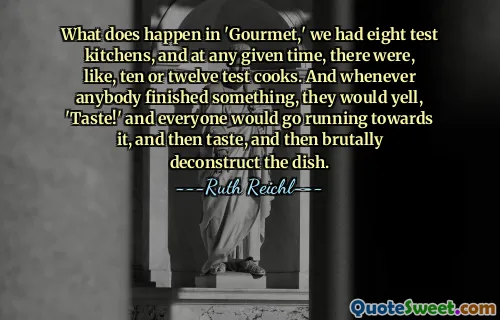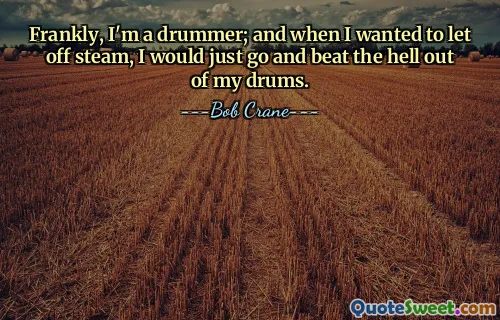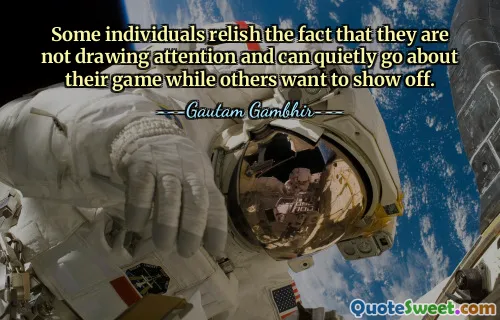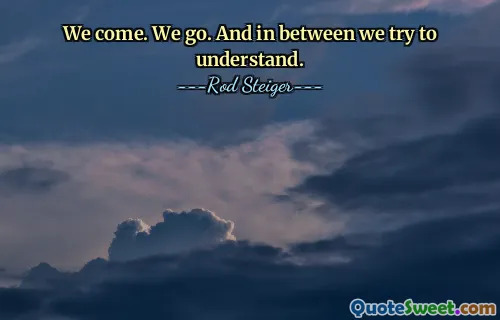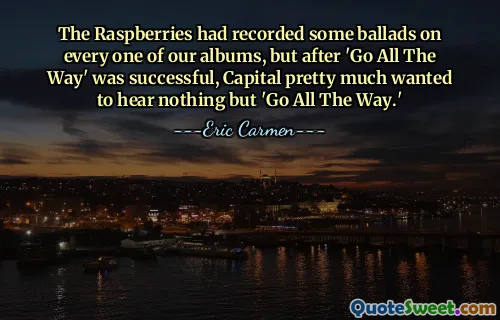正在加载...
查看更多 »
Today Birthdays
1940 -
Arlie Russell Hochschild
1929 -
Martin Luther King, Jr.
1914 -
Etty Hillesum
1908 -
Edward Teller
2004 -
Grace VanderWaal
1984 -
Ben Shapiro
1931 -
Thomas Hoving
1988 -
Skrillex
1963 -
Bruce Schneier
1906 -
Aristotle Onassis
1947 -
Pete Waterman
1850 -
Sofia Kovalevskaya
1979 -
Drew Brees
1941 -
Captain Beefheart
1791 -
Franz Grillparzer
1974 -
Rachel Roy
1960 -
Kelly Asbury
1948 -
Tadashi Shoji
1844 -
Cole Younger
1918 -
Gamal Abdel Nasser
1909 -
Gene Krupa
1893 -
Ivor Novello
1949 -
John Podesta
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