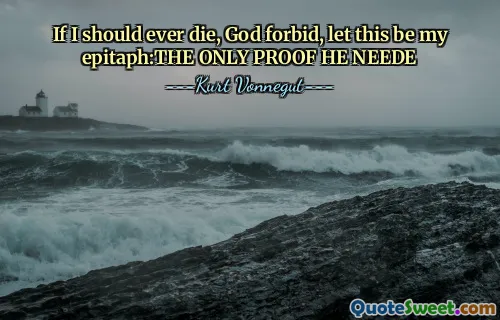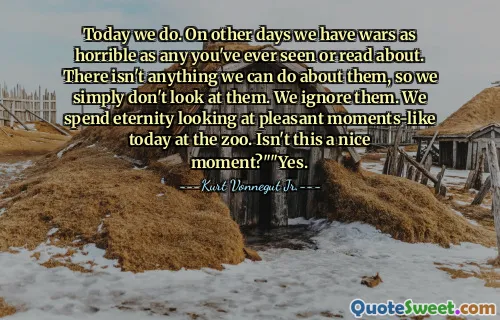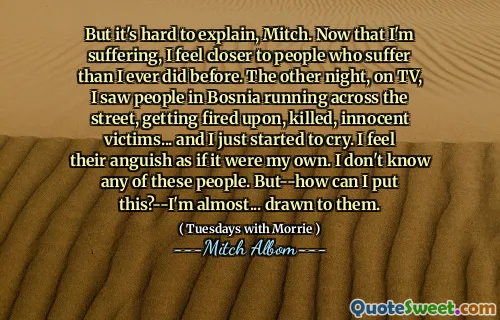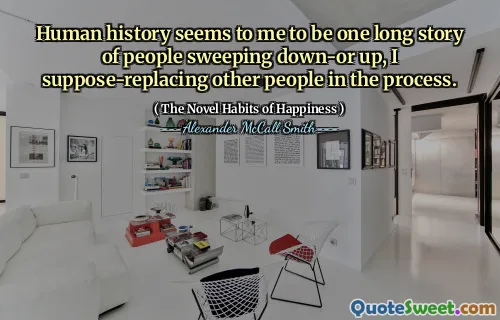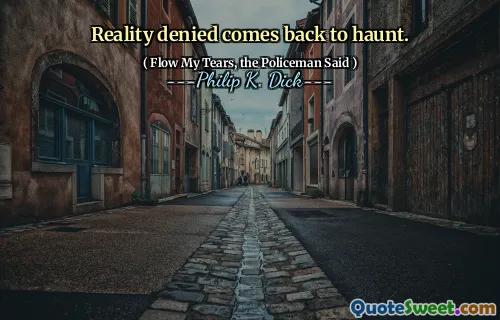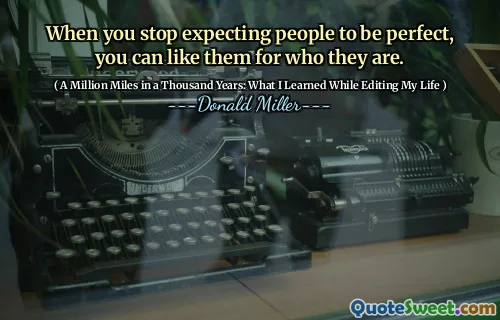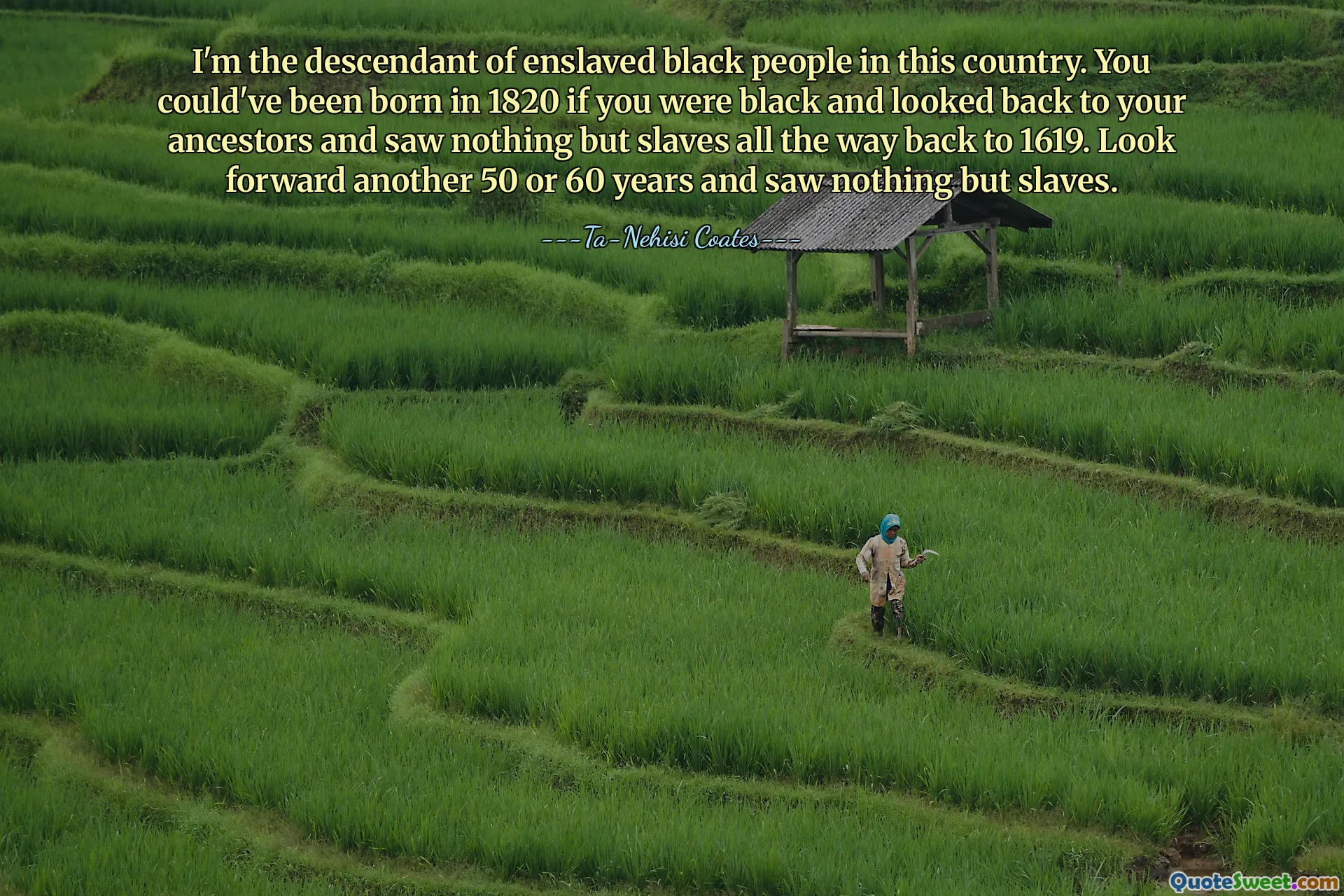
我是这个国家被奴役的黑人的后裔。如果你是黑人,你可能出生在 1820 年,回顾你的祖先,从 1619 年起,你只看到了奴隶。再展望 50 或 60 年,你看到的除了奴隶之外什么也没有。
(I'm the descendant of enslaved black people in this country. You could've been born in 1820 if you were black and looked back to your ancestors and saw nothing but slaves all the way back to 1619. Look forward another 50 or 60 years and saw nothing but slaves.)
这句话有力地强调了非裔美国人所经历的深刻而不间断的束缚遗产。它促使我们反思代代相传的历史的分量,强调许多美国黑人的历史与奴隶制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这一残酷的篇章即使在今天也塑造着身份和意识。有人声称他们的祖先可以追溯到 1619 年,那一年,第一批被奴役的非洲人被强行带到后来的美国,这一说法突显了深深植根于这个国家结构中的系统性压迫。了解这种历史连续性对于理解黑人社区所面临的持久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影响至关重要。它挑战了一种错误观念,即奴隶制只是遥远的过去或很久以前就结束的一章,相反,它表明奴隶制的遗产仍然存在于代际创伤、不平等以及持续不断的争取正义和平等的斗争中。认识到这一血统需要对创伤的共同承认,但也需要对根植于历史背景的正在进行的民权斗争有更深的同情心。这句话还引发了人们对身份的反思——不仅将自己理解为一个个体,而且将自己理解为一个由逆境恢复力所形成的长期连续体的一部分。这种反思可以提高人们对系统性不平等的认识,并激励集体努力实现治愈和正义,承认过去的伤痕继续影响着现在。